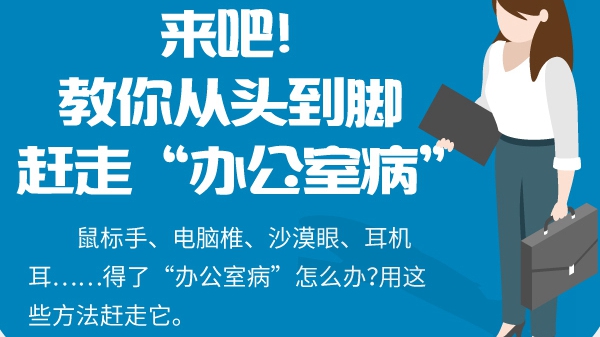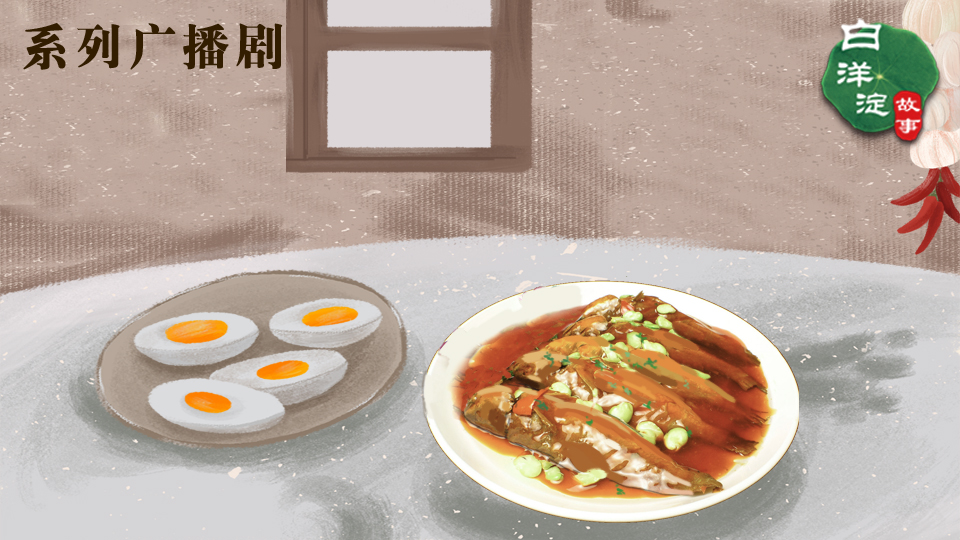孙晓忠
他执着于中西方文化的研究,在学术上硕果颇丰,反响较大;他反思新中国“人民文艺”的成功经验与遭遇难题,并关注国内年轻学人的最新成果。在雄安籍作家李素荣的长篇历史小说《雄安刘因》出版之际,记者采访了他——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孙晓忠教授。
记者:请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和研究的领域?
孙晓忠:我200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,同年分配至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。当时,这个系是国内首家文化研究系,与许多国内外的著名思想家、艺术家合作研究,主要研究当代文化、流行符号、文化生产机制以及城市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。2010年,我转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,主要研究左翼批评理论、延安乡村文化建设,以及上个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。
记者:请你谈谈文学在文化传承的地位或意义?
孙晓忠:以往,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流,往往只是社会少数几个精英人士,往往忽略大多数人的情感生活,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。但是,历史的舞台不能只有帝王将相,因为舞台只有演员没有观众,同样会因缺憾而不完美。文学和思想、文学和理论的不同在于,它在历史书写的不经意之处留下了社会风俗和地方性知识。鲁迅强调文学“为市井细民写心”,也是强调了文学写了作为正统之外东西。《诗经》中有精致的“雅”的文学和高亢的“颂”正统文学,也有歌颂民间疾苦,甚至本身就是下里巴人口里的“文艺”。而后者对于人民文艺、对于文化精神传承更有价值。今天,需要我们思考的是:何种文学书写?传承何种文化?
记者:据悉,你对雄安籍作家李素荣的长篇小说《雄安刘因》提出了许多建议,请谈谈你对这部小说的看法?
孙晓忠:《雄安刘因》一书是近年来写燕赵儒学、写雄安刘因家族历史的第一部。这部历史小说回应了今天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历史的命题,可以说是开创性的。该书在选取的历史时段、地域空间上比较特别。小说中刘因生活的背景是宋元更替、元朝灭宋、宋元转型这一民族融合时期。小说一方面写元朝开国后,理学如何由南向北方转移,另一方面因元朝废除科举取士制度,文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。与南方文人不同,刘因家族虽为儒学世家,但也不是显赫的家族,到刘因父亲刘述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,刘因一生生活贫困,但是依旧不被仕途所动,为当地教育事业与民众求知而躬耕教学,并最终选择做“不召之臣”。
写儒学大师往往容易用精英化的视角来塑造形象,而这部小说的长处,就是将理学家放到日常生活中来写。《论语》中也有孔子游历中的百姓日常故事,并用这些故事来晓喻道理。这部小说有故事的地方往往让刘因形象有血有肉,这是作者所具有的文学基础与写作热情的展示。她喜爱古代诗文,认真钻研与刘因相关的元史,对刘因的生活经历下了一番功夫。如与几个儒学大家的交往,展开学术探讨交流、和关汉卿的相遇而展示的传奇、三台书院招收特殊学子所带给人的震撼等都颇有意思。当然,作为历史小说,有关刘因日常生活的故事可以不必拘泥于历史真实,这就像小说中刘因肯定智存画雪,要写出人物的神似,“画出生命”。雄安的世情风物,还可以再丰富一些,人物和叙事线索,甚至松散闲笔也可以再多一点。这样,小说就更纵横开阖,视野更宽,写得更活。
记者:请你谈谈雄安人写雄安先贤的意义?
孙晓忠:李素荣是一个有文学理想和历史抱负的雄安人,寻找历史传统,对认识雄安,建设雄安必然有意义。离开历史传统谈文化创新是空中楼阁。认识脚下的土地,发掘地方性知识,这些口号从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就开始了,只不过寻根文学的追寻过于抽象,带有深深的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印记,从韩少功《马桥词典》开始,发掘地方特殊的文化,就越来越接地气了。如书写雄安历史,曾有白洋淀作家群等,就体现了革命文学的地域特色。
近年来,不少作家开始阅读地方志书、民间笔记小说,从中寻找创作灵感。李素荣写燕赵大地,选题有特点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前很多作家往往仅仅落笔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奇风异俗,那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。如何将文化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,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比较困难。在这点上,我很欣赏小说中对燕赵学人的家国情怀的理解。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,其实质就是忧患意识的展示。它体现对民族、国家、人民的命运及利益的强烈责任感与深沉的终极关怀。
记者:你对未来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有何建议或期望?
孙晓忠:现代化进程中大城市病是世界性难题,设立雄安新区是探索21世纪智慧城市的重要举措。可以预见,它必然会坚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“中国经验”基础上,汲取近年来学术界城市研究的成果,在广泛参照世界各类城市发展模式和理念的基础上,探索出一条新型城市的发展之路。
城市规划背后体现人的价值观,而好的城市空间必须有好的文化来填充。优秀的文化来自顶层设计的价值观和世界观,而且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地分享并积极赞同。好的文化是粘合剂,它将全体公民粘合为一个共同体。(记者 王渊)